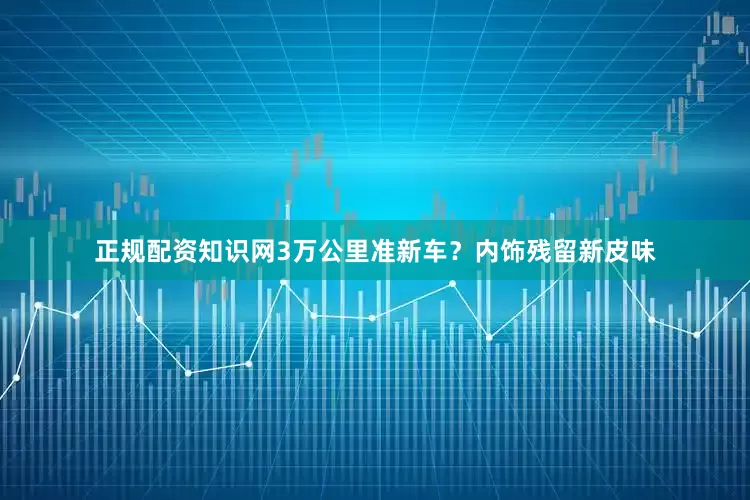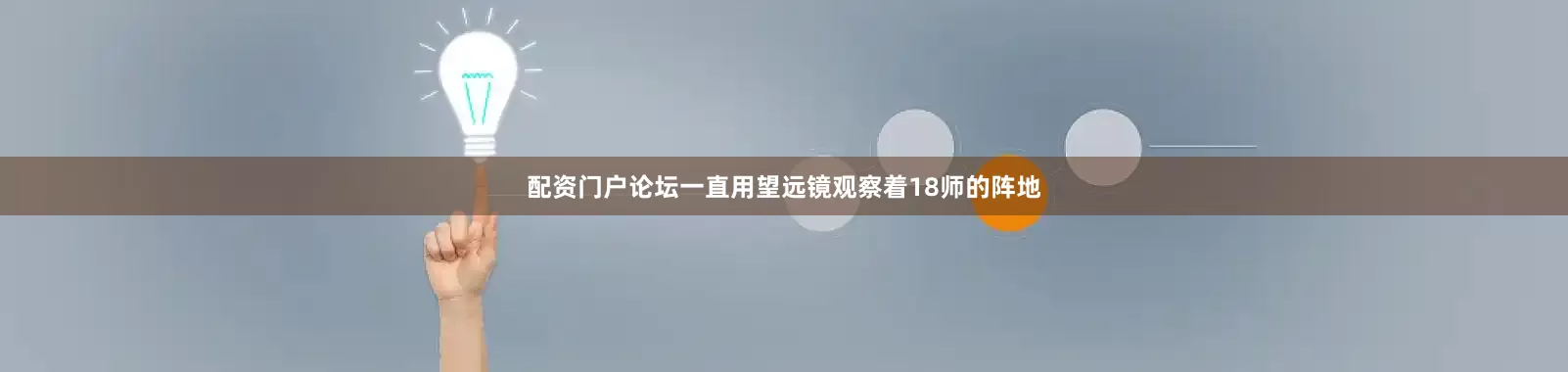
01
1934年10月16日凌晨,贵州石阡县龙塘镇,浓雾如同灰白色的幕布笼罩着山谷。
红18师师长龙云站在队伍最前面,他的军装早已被露水打湿,脸色在晨光中显得格外苍白。昨夜的桐油事件让全师上下都在腹泻,包括他自己在内,几乎一夜未眠。但此刻,他必须挺直腰杆,因为身后还有800多双期待的眼睛。
“师长,总部的电报。”通讯员小李跑过来,手里攥着一份刚收到的电文。
龙云接过电报,借着微弱的晨光仔细看了两遍。电报是萧克军团长发来的,内容很简单:18师负责掩护主力转移,务必拖住追兵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龙云在心里默念着这个数字。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以800人的残部,去阻挡十几个团的敌军。这几乎是一道必死的命令。
他慢慢折起电报,塞进上衣口袋,然后转身面对自己的部下。这些跟随他南征北战的战士们,最大的不过三十岁,最小的司号员何步荣才刚满十五。他们的眼神中有疲惫,有虚弱,但更多的是坚定。
“同志们,”龙云的声音在晨雾中显得格外清晰,“主力需要我们掩护撤退。敌人至少有三个团正在逼近。”
没有人说话,只有远处传来的鸟鸣声打破寂静。
“我不瞒大家,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战。”龙云顿了顿,“但只要主力能安全转移,我们的牺牲就是值得的!”
52团团长田海清第一个站出来:“师长,18师从来就没有孬种!别说三个团,就是三十个团,我们也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红军!”
“对!跟他们拼了!”战士们纷纷响应,虚弱的身体似乎在这一刻爆发出了无穷的力量。
就在这时,前方侦察兵急匆匆跑回来:“报告师长,敌军先头部队距离我们不到两里地!”
龙云深吸一口气,抽出腰间的驳壳枪:“52团跟我上,务必把敌人死死钉在这里!其余各部,按计划掩护总部撤退!”
枪声很快响起,在山谷中回荡。敌人显然没想到会在这里遭遇如此顽强的抵抗,第一波进攻就被打了回去。龙云趴在一块岩石后面,一边射击一边观察战场形势。他看到主力部队正在快速通过渡口,心里稍微松了口气。
但这种喘息是短暂的。很快,更多的敌军涌了上来。他们采用人海战术,试图用数量优势压垮这支孤军。子弹在头顶呼啸而过,不时有战士中弹倒下,但阵地始终没有失守。
“师长,我们的弹药快打光了!”一个连长爬过来报告。
龙云看了看表,才过去一个小时。他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2
时间回到三天前,红六军团指挥部。
任弼时、萧克、王震三位领导围坐在一张简陋的木桌前,桌上摊着一份皱巴巴的地图。朱德总司令的电报就放在地图旁边,上面的内容让三人眉头紧锁。
“总司令说桂系已经停止追击,让我们改变方向,向江口移动,与贺龙的二军团会合。”任弼时缓缓说道,手指在地图上比划着,“但这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西渡乌江的计划。”
萧克摇摇头:“政委,我总觉得不对劲。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都是老狐狸,怎么会轻易放弃追击?万一这是个陷阱怎么办?”
“我同意萧军团长的看法。”王震也开口道,“如果我们改变方向,很可能会陷入桂、湘、黔三省军队的包围。到时候,六军团就危险了。”
任弼时沉默了许久,最后还是拍板:“中央的命令必须执行。不过,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就这样,红六军团改变了行军方向。而就在他们调整路线的同时,蒋介石正在南京发出一道道严令,要求桂系必须继续追击,“不得有误”。
收到命令的桂系将领立即调转方向,会同湘军和黔军,在乌江东岸布下了一个巨大的口袋。红六军团就这样一头扎了进去。
10月15日夜,龙塘镇。
龙云坐在一间破旧的民房里,正在研究地图。他的18师已经连续行军三天,部队疲惫不堪。更糟糕的是,今晚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师长,出大事了!”炊事班长老张慌慌张张跑进来,“兄弟们吃了晚饭都在拉肚子,连站都站不稳!”
“怎么回事?”龙云腾地站起来。
“我…我们在镇上买油的时候,可能…可能买错了。”老张支支吾吾地说,“那个老板说是菜油,谁知道是桐油…”
桐油!龙云的脸色瞬间变了。桐油是用来做防水涂料的,误食会导致严重腹泻。他立即冲出门外,只见整个营地里到处都是捂着肚子的战士。

“师长,我…我不行了…”一个小战士蹲在墙角,脸色惨白。
龙云扶起他:“坚持住!明天还有硬仗要打!”
他连夜召集各连排长开会:“现在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但明天的掩护任务不能有任何闪失。我知道大家都很难受,可是想想主力的几万兄弟,想想我们的革命事业,这点苦算什么?”
“师长,您也中招了吧?”田海清关切地问。他看到龙云的额头上布满了冷汗。
“我没事。”龙云摆摆手,“都回去准备吧,天一亮就是生死之战。”
那一夜,整个18师几乎无人入眠。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腹泻。直到天将破晓,症状才稍有缓解。
03
10月16日上午,战斗进入白热化。
萧克站在渡口对岸,一直用望远镜观察着18师的阵地。他看到那些瘦弱的身影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依然坚守,心里既感动又焦急。
“49团呢?让他们立即回援18师!”萧克对身边的参谋说。
“军团长,49团已经走远了,现在调回来至少需要一个小时。”
“那就快去!告诉团长罗梓铭,无论如何要把18师的兄弟们救出来!”
此时的龙云并不知道援军正在路上。他只知道,阵地上的兄弟越来越少,而敌人却越来越多。
“师长,西南方向又来了两个团!”侦察兵的报告让情况雪上加霜。
龙云咬咬牙:“田海清!”
“到!”
“你带一个连去西南方向,无论如何要挡住他们!”
“是!”田海清二话没说,点了一个连的兵力就冲了出去。
就在这时,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传来——49团的一个营回来了!
“龙师长,罗团长让我们来接应你们!”带队的营长气喘吁吁地说。
龙云眼中闪过一丝亮光,但很快又暗了下去。他看了看四周的形势,敌人已经形成了三面包围,如果现在撤退,必然会暴露主力的行军路线。
“兄弟,你们来得正好。”龙云拍拍营长的肩膀,“帮我们打开一个口子,我们从另一个方向突围。”
“另一个方向?”营长愣了,“那不是相反的方向吗?”
“对,就是要让敌人以为我们走错了路。”龙云苦笑道,“这样他们就不会去追主力了。”
营长明白了龙云的用意,眼圈一下子红了:“龙师长,这样你们就…”
“别说了,这是命令!”龙云打断他,“回去告诉萧军团长,18师完成了任务!”
在49团那个营的掩护下,18师残部成功突出重围。但他们没有向西追赶主力,而是向东南方向——甘溪槽村的方向急行军。
身后,十几个团的敌军像疯狗一样追了上来。
04
甘溪槽村,一个普通的山村,世代以种地为生。村民们从没想到,战火会烧到这个偏僻的角落。
“快跑!当兵的来了!”一个放牛的孩子慌慌张张跑进村里。
村长陈大爷连忙召集村民:“都躲到山上去,等打完了再回来!”
就在村民们准备撤离时,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出现在村口。领头的正是龙云。
“老乡,别怕,我们是红军!”龙云赶紧说明身份,“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陈大爷半信半疑地看着这些疲惫不堪的战士:“你们…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需要一个向导,带我们走出这片山区。”龙云说,“放心,我们会付钱的。”
一个叫李老三的村民自告奋勇:“我带你们走,我熟悉这里的路。”
然而,李老三其实只是在这一带打过几次猎,对山路并不是特别熟悉。在他的带领下,队伍几次走了回头路,最后竟然走上了困牛山。
困牛山,海拔只有几百米,但地势极其险峻。三面都是悬崖峭壁,只有来路一条小道。当地人之所以叫它困牛山,就是因为牛上去了就下不来,会被活活困死。
“这…这里走错了。”李老三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困牛山是死路啊!”
龙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但就在这时,他注意到山崖边有很多粗壮的藤蔓。
“这些藤蔓结实吗?”他问李老三。
“结实是结实,我们打猎时经常用它们下崖。但是…但是人太多了,而且你们还有伤员…”
龙云没有再问,他知道已经没有选择了。身后的枪声越来越近,敌人马上就要追上来了。
“所有人听令!”龙云大声说,“能爬的都顺着藤蔓下去,向思南方向突围!伤员和我留下,掩护大家撤退!”
“师长,我留下!”田海清第一个站出来。
“我也留下!”
“还有我!”
战士们纷纷请战,没有一个人愿意先走。
龙云的眼睛湿润了,但他必须下决心:“这是命令!田海清,你带一半人留下,其余人立即下山!”
就这样,200多人开始顺着藤蔓向崖下爬去。而龙云和田海清则带着剩下的100多人,在山顶布置防线。
敌人很快就冲了上来。由于地形狭窄,他们无法展开兵力,只能一波一波地往上冲。红军战士们居高临下,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弟兄们,给我冲!谁先攻上去,赏大洋五十块!”敌军团长在山下声嘶力竭地喊着。
但是没用,困牛山的地形太险要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眼看着天色渐暗,敌军团长急了,他想出了一个歹毒的计策。
“去,把附近村子里的老百姓都给我抓来!”
很快,甘溪槽村的几十个村民被五花大绑地押到了山下。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妇女,还有十几岁的少年。
“红军听着!”敌军团长拿着铁皮喇叭喊道,“你们不是说为老百姓打天下吗?现在我就让这些老百姓走在前面,看你们打不打!”
山顶上,龙云和战士们看到这一幕,全都愣住了。
“畜生!”田海清咬牙切齿地骂道,“他们怎么能这么无耻!”
“师长,怎么办?”一个战士问。
龙云沉默了。他看着那些无辜的村民,又看看身边的战士们。这些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现在却要面临这样的选择。
“红军兄弟,不要管我们,打吧!”突然,被押在最前面的陈大爷大声喊道,“我们不怕死!”
“对,不要管我们!”其他村民也纷纷喊道。
但龙云知道,红军绝对不能向老百姓开枪。这是铁的纪律,更是革命的根本。
“所有人听令,”龙云站起身,声音异常平静,“对空鸣枪,不许伤害老百姓。”
“可是师长…”
“这是命令!”
于是,当敌人押着村民往上爬时,红军的枪声依然响起,但子弹都打向了天空。敌人起初还有些畏缩,但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哈哈,他们不敢打!兄弟们,冲啊!”
敌人越来越嚣张,甚至开始推搡村民,让他们走得更快。一个妇女抱着孩子摔倒了,敌兵上去就是一脚。孩子的哭声撕心裂肺,让山顶上的红军战士们红了眼。
“师长,让我冲下去吧!我要跟这些畜生拼了!”一个年轻战士哭着说。
龙云摇摇头:“不行,我们一冲下去,他们就会开枪,到时候老百姓会伤亡更多。”
眼看着敌人越来越近,已经到了不足五十米的距离。龙云看了看身边的战士们,又看了看崖下。他知道,是时候做出最后的选择了。
“兄弟们,”他缓缓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绝不能让人民因为我们而受害。”
“师长,您是说…”田海清似乎明白了什么。
龙云点点头,然后大声说:“所有人听令,砸毁武器!”
战士们虽然不舍,但还是执行了命令。枪支被砸坏,刺刀被折断,手榴弹被拆解。做完这一切,龙云转身面向悬崖。
“红军万岁!”他高呼一声,纵身跳下悬崖。
“红军万岁!”田海清和其他战士也纷纷跟着跳了下去。
被押上山的村民们目睹了这一幕,全都跪在地上痛哭失声。那些敌兵也被震撼了,他们不敢相信,真的有人会为了保护素不相识的老百姓而选择死亡。
05
崖下,黑滩河水被染成了红色。
当甘溪槽村的村民们赶到时,看到的是一幅惨烈的景象。一百多位红军战士的遗体散落在河谷中,有的还保持着跳崖时的姿势。
“快找找,看还有没有活着的!”陈大爷一边哭一边喊。
村民们在乱石和荆棘中仔细搜寻。奇迹般的是,他们真的找到了几个幸存者。这些战士跳崖时被藤蔓缠住,虽然受了重伤,但还有一口气。
其中就包括15岁的司号员何步荣。他年纪最小,身体最轻,跳下去时被一根粗大的藤蔓兜住,摔在了一个斜坡上。虽然多处骨折,但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村民们小心翼翼地把幸存者抬回村里,用土方子给他们疗伤。陈大爷更是把自己家里珍藏多年的草药都拿了出来。
然而,三天后,敌人又来了。他们得到消息,说有红军伤员藏在村里。
“把人交出来!”敌军营长恶狠狠地说,“否则,烧了你们整个村子!”
村民们相互看看,谁也不说话。
“我再问一遍,人在哪里?”
“在我家。”陈大爷站了出来。
敌兵冲进陈家,把几个伤员都拖了出来。这些红军战士虽然遍体鳞伤,但眼神依然坚定。
“说,谁是龙云?”敌军营长问。
“我是龙云!”一个战士挣扎着说。
“我才是龙云!”另一个战士也说。
“你们都错了,我是龙云!”第三个战士大声说。
敌军营长气急败坏,掏出手枪就要行凶。就在这时,他看到了昏迷不醒的何步荣。
“这个呢?”他用枪指着何步荣问。
“他还是个孩子啊!”陈大爷的老伴哭着说,“你们要是连孩子都杀,会遭天谴的!”
其他村民也都跪下来求情:“长官,他才十几岁,求求您放过他吧!”
敌军营长看了看何步荣稚嫩的脸庞,又看看他奄奄一息的样子,最终收起了枪:“算了,反正也活不了几天。其他人,全部带走!”
那几个清醒的红军战士被带走了,临走时,他们用尽最后的力气喊道:“红军万岁!革命一定会成功的!”

后来村民们才知道,这些战士全部英勇就义了。他们至死都没有说出龙云的下落,也没有透露红军的任何机密。
06
何步荣活了下来。
在陈大爷一家的悉心照料下,他慢慢恢复了健康。但当他想要去寻找部队时,却发现已经没有任何消息了。红六军团早已远去,而他一个人,又能去哪里呢?
“孩子,就留在我们家吧。”陈大爷说,“从今天起,你就叫陈世荣,是我的儿子。”
就这样,何步荣变成了陈世荣,在甘溪槽村生活了下来。他娶妻生子,一直活到2001年才去世,享年82岁。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经常会坐在困牛山下,望着那个曾经跳崖的地方发呆。有时候,他会吹起司号,那是他仅存的红军记忆。苍凉的号声在山谷中回荡,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悲壮的往事。
而甘溪槽村的村民们,则把每年的重阳节定为祭拜红军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全村老少都会登上困牛山,在跳崖的地方摆上供品,烧香磕头。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了68年,从未中断。
2002年,石阡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又铸在一次会议上偶然听说了这个奇怪的风俗。出于职业敏感,他立即展开了调查。
通过查阅档案、走访老人、实地考察,杨又铸和他的团队终于还原了这段尘封的历史。他们确认,在困牛山跳崖的正是“失踪”了68年的红18师。
消息传开后,当年红六军团的老战士们纷纷赶到石阡县。萧克将军已经去世,但他的儿子代表父亲来了。王震的秘书也来了。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困牛山下痛哭失声,他们终于知道了当年的战友们去了哪里。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啊!”一位老红军哽咽着说,“为了保护老百姓,宁愿跳崖牺牲。这就是我们红军的本色!”
2004年,困牛山被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山顶上建起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那100多位烈士的名字。其中,龙云的名字排在第一个。
关于龙云的下落,直到多年后才有了消息。原来,他并没有死在困牛山上。
当时,龙云带着200多人顺着藤蔓爬下山崖,试图突出重围。但敌人早有准备,在山下布下了天罗地网。经过一番血战,队伍被打散了。龙云身负重伤,最终被俘。
敌人把他押送到长沙,想要劝降这位赫赫有名的红军师长。但龙云宁死不屈,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都没有让他动摇分毫。
“你们可以杀死我的肉体,但杀不死共产主义的理想!”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龙云如是说。
他被辗转关押在长沙、南昌、九江、武汉等地。每到一处,敌人都会派人来劝降,但得到的永远是同样的回答:“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
1936年3月,在武汉的监狱里,龙云走完了他32年的人生路。临刑前,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在墙上刻下了八个字:“革命必胜,同志们前进!”
行刑的士兵后来回忆说,龙云走向刑场时昂首挺胸,脸上还带着微笑。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声音,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撼。
07
故事还没有结束。
2010年,贵州省委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革命遗址普查。工作组来到石阡县时,意外发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秘密。
在县档案馆的一个角落里,工作人员找到了一个破旧的木箱。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几十封发黄的信件。这些信都是写给“龙云师长”的,但从未寄出。
写信的人叫张德顺,是当年红18师的一个通讯员。1934年10月16日那天,他奉命给总部送信,因此躲过了困牛山的劫难。但当他完成任务返回时,18师已经不见了踪影。
此后的几十年里,张德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部队。他写了无数封信,想要告诉师长,他还活着,他还在等待归队的命令。但这些信注定无法送达,因为收信人早已不在人世。
1985年,张德顺在弥留之际,把这些信交给了儿子,嘱咐他:“如果有一天找到了18师的下落,就把这些信烧给师长和战友们。”
当这些信件被发现时,张德顺的儿子已经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了。他带着父亲的遗愿来到困牛山,在纪念碑前烧掉了所有的信。
“父亲,您可以安息了。”他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师长和战友们都是英雄,他们没有辜负您的期望。”
还有一个人的故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当年带路的向导李老三。
困牛山事件后,李老三一直生活在自责中。他总是说,如果不是自己带错了路,红军就不会陷入绝境。村民们都劝他,说这不是他的错,但李老三始终无法原谅自己。
每年重阳节,李老三都会第一个上山祭拜。他会在山顶上长跪不起,口中念念有词:“龙师长,是我害了你们啊!”
1976年,李老三临终前,他让家人把自己埋在困牛山脚下。他说:“我要永远给红军守墓,这是我唯一能做的赎罪。”
如今,李老三的坟墓就在山脚下,墓碑上刻着一行字:“红军的带路人李老三之墓”。每年清明节,都会有人来给他扫墓,感谢他为红军做过的事,也原谅他无心的过失。
08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2023年。
困牛山下,一群来自北京的大学生正在进行暑期社会实践。他们的任务是采访当地老人,记录红军的故事。
“奶奶,您还记得当年的事吗?”一个女学生问道。
坐在对面的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她叫陈秀英,是当年陈大爷的孙女。她见证了那段历史,也见证了陈世荣(何步荣)的一生。
“记得,怎么能不记得。”老人的声音有些颤抖,“我那时才几岁,但那一幕永远刻在我心里。那些红军啊,都是好人,为了不让我们受伤害,他们宁愿跳崖…”
说到这里,老人已经泣不成声。
学生们也都红了眼眶。他们无法想象,在那个年代,竟然有人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陈奶奶,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另一个学生问。
老人擦了擦眼泪:“孩子,你们现在可能不理解。但在那个年代,红军是真心为老百姓的。他们宁可自己死,也不愿意老百姓受一点伤害。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啊!”
采访结束后,学生们登上了困牛山。站在当年红军跳崖的地方,他们仿佛看到了那个悲壮的场面——
夕阳西下,晚霞如血。一百多位红军战士站在悬崖边上,他们的身后是穷凶极恶的敌人,身前是万丈深渊。但他们的脸上没有恐惧,只有坚定。
“红军万岁!”
随着这声呐喊,他们纵身一跃,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做人民军队。
风在山谷中呼啸,仿佛是英魂在歌唱。那歌声穿越时空,一直传到今天,传到未来。
困牛山依然矗立在那里,见证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每当夕阳西下,山影斜长,仿佛还能看到那些年轻的身影。他们永远年轻,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而在山脚下的甘溪槽村,那个重阳祭红军的传统还在继续。不同的是,现在来祭拜的不只是本村人,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他们带着鲜花,带着敬意,来缅怀这些为了信仰、为了人民而牺牲的英雄们。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红18师虽然“消失”了68年,但他们的精神永远不会消失。他们用生命告诉我们,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什么是人民军队的本色。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困牛山的壮举,不仅仅是一次军事上的牺牲,更是一次信仰的见证。它告诉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队里,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这就是他们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2023年10月16日,困牛山战斗89周年纪念日。
贵州省石阡县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聚集在困牛山下,共同缅怀那些英勇的烈士。
纪念仪式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是王震将军的儿子,今年也已经80多岁了。他代表父亲,代表所有健在和已故的红六军团老战士,向困牛山献上了花圈。
“我父亲生前经常提起18师的战友们。”老人哽咽着说,“他说,没有18师的牺牲,就没有红六军团的胜利会师。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随后,当地政府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将困牛山建设成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仪式结束后,人们纷纷登上困牛山。在山顶的纪念碑前,大家齐声朗诵着碑文:
“公元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第十八师一百余名指战员,为掩护主力转移,在此与数倍之敌激战。敌以平民为盾,红军不忍伤及无辜,遂毁械跳崖,壮烈殉国。此乃人民军队本色,革命精神永存!”
读完碑文,全场默哀三分钟。山风呼啸,松涛阵阵,仿佛是英烈们在天之灵的回应。
一个小女孩拉着奶奶的手问:“奶奶,他们为什么要跳崖呢?”
奶奶摸着小女孩的头,温柔地说:“孩子,因为他们爱人民胜过爱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共产党人,这就是红军。”
夕阳渐渐西下,把困牛山染成了金黄色。在这片曾经浸透鲜血的土地上,如今已是一片祥和。但那段历史,那种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行。
【参考资料来源】 1.《红六军团长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2.《石阡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杨又铸:《困牛山红军跳崖事件调查报告》,《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
4.《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陈世荣(何步荣)口述,陈国善整理:《我的红军生涯》(未刊稿),石阡县档案馆藏
在线股票配资门户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